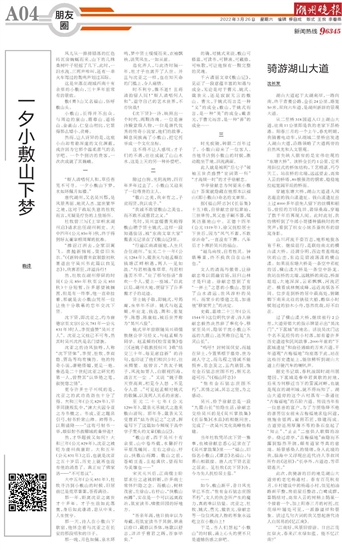晓诗
风儿从一排排错落的红色砖瓦房蜿蜒而来,山下的几株桑树叶子轻摇了几下,此时,一汩水流、三两声哞叫,还有一串火车驾过的轰鸣声划过耳际。
这是坐落在湖城西南十有余里的小敷山,三十多年前常有的景致。
敷(旉)山又名福山,俗呼敷山头。
小敷山,长得并不出众。与周边的康山、霞幕山、道场山、金盖山、仁皇山相比,它显得那么矮小、贫瘠。
然而,让人讶异的是,这座小山却有着深邃的文化渊薮,或许因为它那个温柔喜气的名字吧。一个个到访的贵客,一次次成就了其巍峨。
一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
唐代湖州,又名吴兴郡,是风景秀丽、地灵人杰、富庶繁华之地,这对于政坛失意的杜牧而言,无疑是疗伤的上佳场所。
杜牧曾三写《上宰相求湖州启》请求出任湖州刺史。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秋,终于得到好友兼宰相周墀的批准。
“捧诏汀洲去,全家羽翼飞。喜抛新锦帐,荣借旧朱衣。”(《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欣喜若狂,洋溢诗行!
然,杜牧在湖州停留的时间(公元850年秋至公元851秋)十分短暂,许多愿望被搁置,但是有一件事,他一直牵挂着,那就是去小敷山凭吊一位让他十分敬慕的忘年交沈下贤。
沈下贤,即沈亚之,约为唐德宗至文宗(公元781年—公元831年)时人,李贺盛赞“吴兴才人”。沈亚之父祖己不可考,然其时吴兴沈氏是名门望族。
沈亚之的诗风独特,人称“沈下贤体”,李贺、杜牧、李商隐、贾岛等均有模仿。他的传奇小说,凄艳怪媚,更是一绝。鲁迅是二十世纪沈亚之研究的第一人,曾赞其“以华艳之笔,叙恍惚之情”。
更令许多士子兴叹的是,沈亚之的武功造诣也十分了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平李同捷叛乱中,“谏大夫因令亚之为书檄之。书成,亚之题帛引弓,射书於常山帅。帅得书,以期请降……”这弯弓射书一举,颇似射书救聊城的鲁仲连!
然,才华超拔又如何?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沈亚之被贬为虔州南康尉。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之后,也就是沈亚之五十岁后,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真正应了佛家语——“不可思议”。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杜牧寻访到小敷山的时候,旧居前已是荒草萋萋,苍苔满径。
那一年,距离沈亚之离世才十多年。才子生前如此落寞,身后如此凄清,悲从中来,人生恍兮。
那一天,诗人在小敷山下歇宿,他怀念着与沈亚之在长安的那段唱和的日子。
那一晚,月色如佩,泉水环鸣,梦中贤士缓缓而来,衣袖飘袂,谈笑风生,一如从前。
造化弄人,与此诗时隔一年,杜才子也离开了人世。并且与沈亚之一样,也在知天命的门槛上,令人痛惜。
时不利兮,骓不逝!且将清韵留人间!“斯人清唱何人和”,退守自己的艺术世界,不亦快哉!
《沈下贤》一诗,映照出一个时代、两颗诗魂。一位是唐诗殿堂级人物,一位是唐代优秀的传奇小说家,他们的故事,瞬息间拔高了小敷山,把它托举成一个文化坐标。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才子们的不遇,往往成就了山山水水,这是上天的另一种补偿吧。
二
隙过白驹,光阴流转,四百年多年过去了。小敷山又迎来了一位尊贵的主人。
“敷山之美,我幸有之,子贫而贤,我以成子。”
“我诚不敢望敷山之美也,而不敢不成曹君之义。”
元时,吴兴富儒曹元购得敷山赠予贤士姚式,这样一段知遇佳话,被“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记录在了《敷山记》里。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戴表元与赵孟頫在钱塘江畔相遇,两人一见如故。“与君相逢难草草, 与君相逢苦不早。”应了那句俗语“喜欢一个人,爱上一座城。”自此以后,湖州大地,便留下了许多戴才子的足迹。
贤士姚子敬,即姚式,号筠庵,生卒年不详。姚式与赵孟頫、牟应龙、钱选、萧和、张复亨、陈慤、陈康祖,被后世并称为“吴兴八俊”。
姚式早年曾跟随吴兴硕儒敖继公学习经义,与赵孟頫为同学。赵孟頫的《松雪斋集》卷三《送姚子敬教授绍兴 》载“结交三十年,每见意自新” 的诗句,也印证了他们相识少时,往来频繁。赵曾言,“我友子姚子,风流如晋人,白眼视四海,清言无一尘 。” 又说 “姚子敬天资高爽,相见令人怒 ,不见令人思 。”可见赵孟頫对姚式的敬佩,以及两人关系的亲密。
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戴表元承姚式之邀来敷山游玩。那年冬,戴表元又受曹君“姑为我记之”之请,挥毫写下了这篇如今频现于高中学子案头的文章《敷山记》。
“敷山者,西于吴兴十有余里,山中卷外截,水罄折行平原茂樾间。左右之徐山、杼山,挟敷山而蹲。敷山之前,苍峭亘连,圭起虡伏,望而知为美壤也……”
宋灭元兴后,江南儒士阶层求仕之途被斩断,许多南士常怀归隐之念。而敷山,树林茂密,左徐山,右杼山,“挟敷山而蹲”,实在是一个可以远离政治,筑室读书,啸傲田园的好地方。
“吾亲年髙,他日倘幸以为寿藏,而筑室读书于其侧,耕渔以给口,藏修以养体,咏歌以舒志,洋洋乎曹君之赐,吾事毕矣。”
的确,对姚式来说,敷山可修墓,可读书,可耕渔,可藏修,可咏歌,可让他保有一颗完整的灵魂。
千古清丽文章《敷山记》,见证了一段意蕴丰富的知遇与成全,无论是对于曹元、姚式、戴表元,还是寂寂无言的敷山。曹元,于姚式而言是一种“义”的成全;敷山,于姚式而言,是一种“美”的成全;戴表元,于曹元而言,是一种“善”的成全……
三
时光疾驰,转眼二百年过了。小敷山迎来了一位客人。当他寻访到小敷山的时候,激动跪坐于地,泪流满面。
此人就是被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盛赞“宏词第一科”“才高倾一时”的才子徐献忠。
华亭徐献忠为何要来小敷山?答案就隐藏在他那本以福山(即小敷山)命名的文章里。
据《福山阡志》(《长谷集》十五)载,自徐献忠曾祖辈始,三世单传,其父患子嗣不蕃,嘱其访墓地山中。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徐父抚松居士下世后,因为“风气不蓄,不敢虚治命”,一直没有下葬。八年后才卜葬於吴兴的福山。
“越鸟南枝,自有性灵。钟鼎尊重,终不换我自在山林也。”
文人的清高与傲骨,让徐献忠难以圆融官场,回归山林才是归途。徐献忠想到了有“一抔土”之恩的小敷山,想到了山水清远、世风淳朴的吴兴。而家乡的倭寇之乱,加速他“移家霅上”的决定。
史载,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这位明代学者、诗人徐献忠毅然决然辞了奉化令,移家至吴兴,隐居于离小敷山不远的九霞山,还笑称自己是“九灵山长”。
“呜呼!封树虽仅安,而越在异土,今置果橒于墓旁,世为湖人守之,而乌程之情诚不能捐弃,思念及之,五内崩裂,惟有金石铭志庶图不朽,惭无名迹可污。”(《福山阡志》)
“惟有金石铭志庶图不朽”,其情之诚,其志之坚,为之感动。
吴兴,给予徐献忠是一段“九霞山长”怡隐生活;徐献忠交给吴兴的是《吴兴掌故集》《长谷集》《水品》的相继问世,完成了一次吴兴文化高峰性构建。
当年杜牧凭吊沈下贤一雅事,也被徐献忠悉心记录在了《吴兴掌故集》里——“福山,旧俗名小敷山,《谭志》名福山,与旉山相联接。唐人沈下贤名亚之居此。见杜牧《沈下贤》诗,今为先人抚松居士墓。”
……
如今,敷山渐平,昔日风光早已不在。“惟有金石铭志庶图不朽”,文人的执念所产生的魔力,真的难以估量。沈亚之、杜牧、姚式、曹元、戴表元、徐献忠等一位位风流人物的形象永远屹立在小敷山上!
于是,当人们想起“小敷山”的时候,涌上心头的便不只是遗憾伤感之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