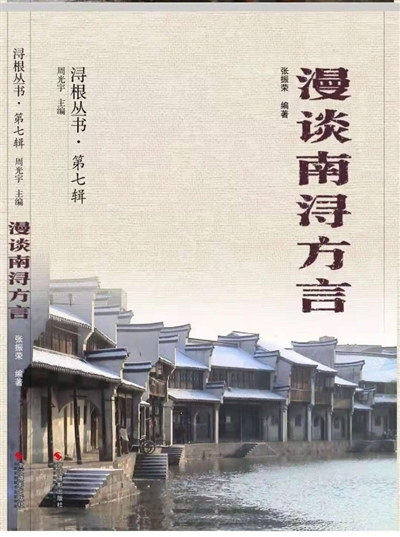陆士虎
古人云:“礼失诸野,善在黎民。”
一位年已古稀的文化老人,近年来行走在江南水乡南浔的阡陌间,寻访最会说南浔方言的人,捕捉有关南浔方言的资料,用纸笔或电脑、手机记录,探求在这个特殊汉语的世界。现在,他在抗击新冠疫情的非常时期,经过三个多月的艰难拼搏,推出的南浔方言研究的第一部作品《漫谈南浔方言》(浙江摄影出版社,2020年12月第一版),面世了。
这位文化老人,就是我的同窗、文友、邻居阿振(张振荣的乳名)。也许是母亲的启蒙教育,方言的种子从小就在他心田扎根。十年前,他在家庭的阴影里写下了第一篇有关南浔方言的心得,后来又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趣谈南浔方言的短文,还应邀为南浔区档案局当了一回“浙江记忆工程重点项目”方言语言发音人。在正式录音录像之前,他和尔康还进行了培训和演练,邀请我和嘉允兄加盟,对照《规定文本》逐字逐句推敲。据阿振回忆,他和尔康去湖州一家工作室“定稿”时,心情是很不平静的。面对灯光摄像,好不容易唸完了《规定文本》的声韵调、词汇和短文,已折腾出一身汗来。事后,他在桐乡儿子家里为《规定文本》进行同音汉字标注,用快递寄出时,才舒了一口气。
阅读阿振的新书《漫谈南浔方言》,仿佛与他面坐聊天,亲切、熟悉、有趣、好看、逗笑,又不时感到陌生、惊喜。我认为书名的“漫谈”一词颇为贴切,既打破了文本的束缚,可以自由发挥,侃侃而谈,又蕴含谦虚、低调之意。也就是说,这仅仅是探索性的一家之言。顺着“漫谈”的思路,他开卷就提及杭州、上海的方言,虽与南浔方言存在差异性,但也有很多相同或相近之处,毕竟他们都是吴方言的子民。南浔方言,或称“闲话”“土话”“土音”,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因为方言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越多的包容性越能显示出其魅力,在必要时写进课本,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进行方言的学习和传播,也无尝不可。我总感到,南浔方言的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浓浓的地方文化气息,轻声细语,糯软顺口,风情万种,蕴含着浔溪水一样的柔情。南浔方言的这种特征,是与江南水乡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有关。可以说,品读《漫谈南浔方言》这部新书,犹如翻阅着南浔一篇篇文化的纪事,倾听着南浔一页页历史的回声。
一方语言,即一方文化,传承语言,就是传承文化。南浔现属浙江省湖州市所辖,地处太湖南岸,与上海、杭州、苏州都相距不远,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文化灿烂,人才辈出,是美丽、繁华的江南水乡。阿振说,南浔方言是吴方言的一个小小分支,隶属于吴语区太湖片(即北部吴语)湖州小片(苕溪)方言。他由此阐述了南浔闲话与湖州小片方言,以及南浔方言和周边吴方言小片方言的异同举例。但由于南浔历史上一直处在吴、越、楚边界,且地域归属多变等原因,故而南浔话中掺杂着越语、楚音或其它成分。其中又不仅仅是各地的吴方言,甚至与最典型的吴语——苏州话,也颇具差异。同样的道理,南浔方言还受上海话影响。特别是上海开埠以后,随着“西风东渐”,南浔话里也夹进了许些“洋”东西。改革开放以来,南浔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与外部世界交流融合,南浔话中又溶入了很多时髦的新元素。这说明方言本身就是一条变化着、流动着的河。
南浔方言文化内涵丰厚,可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第四章中,阿振经过搜集、筛选和整理,给我们娓娓动听地讲述了许多南浔方言的传说、故事、轶事和趣闻,如“十家香”“请媒人”“弯转”以及富有时代感的小插曲等等,诙谐、幽默、风趣、生动,且可读性增强。第五章是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南浔方言童谣和谚语。仅是谚语类,就有气象谚语、农事谚语、生活谚语、人生哲理谚语、行为规范谚语等好几种,还有动物入谚。第六章是南浔方言的词语归类。方言词的集萃,即一二三四及五字以上词语和歇后语、隐语,宛如五色斑斓,丰富多彩。虽有借鉴的基础,但也富有创新。阿振说,即使这样,还难避“挂一漏万”之嫌。这说明南浔方言仿佛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藏”,“掘宝”人工作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而南浔方言中很多语音都是古音,自然也含有古义。在这部书中,有关南浔方言的古音古义的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有的方言不一定是古音,但古义是十分清晰的。还有一些特有的表述,如“老娘家”,从字面上解释是老一辈的娘家,其实正确的所指是“父亲”。 第七章是南浔方言的语法特点及其它。毋庸置疑,南浔方言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进化、演变中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它的语法和普通话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现代汉语各种方言之间的差异性主要是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其中语音尤为突出。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多数方言和共同语言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独立的语种。但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广普通话,方便东西南北各方言区人交流,惠及当代,功在千秋,我们应当努力推行并普及光大。同时,从方言的特点和进化、演变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到人类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南浔方言是弥足珍贵的地方特色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和民族遗产。故而《漫谈南浔方言》,这部新书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当下研究南浔丰厚的历史文化,也有助于学校开设“拓展性”课程,是中小学教师必不可少的乡土教材参考书,还是本土作家、诗人的“语言库”。也许因为我和阿振都是文学写作的爱好者,所以总想让方言与文学扯上点边。方言之于文学,好比盐之于饭菜。一顿饭有各种吃法,可总少不了一点盐,有了盐才有味道。中国四大名著,哪一部不是包含着南腔北调的方言风味?哪一部不是总有一点增色添香的方言桥段?《西游记》,有诙谐风趣的淮安方言;《水浒传》有豪爽劲道的山东方言;《红楼梦》更是集各地方言之大戏,苏北、常州、南京、北京等地的方言大放异彩。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老舍的“京味儿”,张爱玲的海派方言,沈从文用湘西方言写诗,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陕军”崛起,其代表作《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无不让读者在《秦腔》中品悟到“最美的平凡”。土生土长的南浔作家柳湘武,自然而然也把盐撒进了自家的作品里。他在长篇小说《流年如梦》中采用了不少南浔、苏州方言,不是另一种本土的印证吗?
我曾多次与阿振讨论方言,旨在加深对他这部新书的理解。阿振感叹说,语言文化遗产有特别重要的保护价值。这首先在于语言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性:它既是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是特定族群文化的重要部分,体现着一个族群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和成果,通常被当作构成一个民族的标志性元素之一;同时,语言作为其它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一个族群在长期的历史过程积累的大量文化语言。汉语的各种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也是普通话健康发展的资源和保障。听此,引起我的联想和思考:方言所体现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根脉。说着不同方言的人,会有旁人无法体会的心灵黙契,留住方言就是留住乡音,因为方言里有着普通话无法传递和表达的妙处。
当前,在南浔方言和其它方言一样“渐渐淡化”之际,保护、抢救地方方言使其代代相传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和社会担当。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挖掘、整理和研究地方方言。在此意义上,阿振率先走出了一大步,通过他的辛勤耕耘,终于填补了南浔史上比较全面、系统研究南浔方言的空白。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在留住方言的努力上,应该说《漫谈南浔方言》是会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