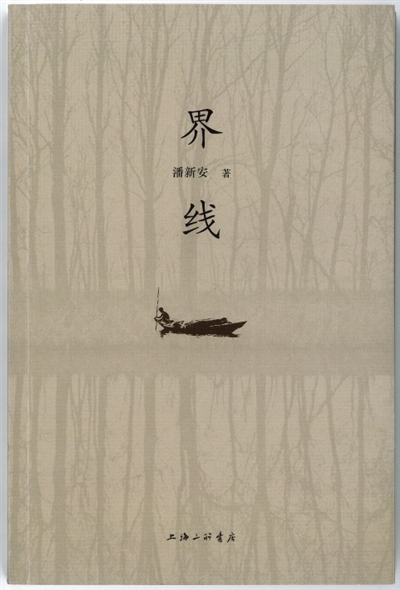李浔
真诗人与伪诗人的区别在于,真诗人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而伪诗人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在世界诸多公共危机面前,真诗人的立场是真善美,而伪诗人是假虚空,一目了然。2008年—2010年笔者曾在一个文学网站当版主时,湖州的潘新安似乎每天来逛论坛并且贴诗,他的诗有主动介入社会热点、难点意识的特征,现在还是这样。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潘新安每天写诗,至今《隔离时期的诗篇》这个组诗已写了59首。这些诗直面现实,或对人性的剖析、或对虚伪、墮落的社会现象的批判,表达了一个诗人应有的良心写作的态度。
1969年出生的潘新安,他身上有着“60后”诗人明显的主动介入社会意识的特征。在他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诗集《界线》中的诗,更说明了这一点。我尽管和他同处一城,偶有相聚,但由于人太多故极少单独谈诗。这次读他的诗集《界线》,也算一次和他的诗的集中交流吧。
潘新安诗集《界线》收入短诗83首,写作时间跨度大约近十年。从内容上看,这些诗展示了潘新安眼中的农村、小集镇以及城市底层的生活,也可以说,这些诗是他的记忆、反思和发现的诗。在创作的观念上,他一贯用经验与反思的理念反映了他阶段性的对自身生活和外部世界的关照。他的诗,给我总体的感受是,直击现实生活本质,对人性的试探有血有肉、更有疼痛感。我以为这是一个优秀诗人的素质。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有关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的争论早已停息,而这十年,诗坛上最热闹的争端是何谓新诗的探讨,是翻译体式新诗,还是用古典观念进入当代现实的新诗。潘新安似乎并不关心这些,这些年他只关照自己的感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体制外诗人,诗歌的语言是口语的,内核是“批判现实主义”。 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贵的不变的立场,他所讲述的现实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悲和痛,这种立场是已锻打过的铁,是钢,也不会生锈。他的《高富路118号》是以一个城市客居者的身份写下的。
整个夏天,只有壁虎
深夜从天花板上摔下来几次,造访我
它总能甩掉它的尾巴
有多少本能,我们也需要
重新学习?
总是换地方都呆不长
谋生,已如同在躲避一场无形的追杀
但是你看我,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革命者——
高富路118号是潘新安从小镇来到湖城后的生活地。这不是一条繁华的路,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和营生,潘新安经营的棋牌室也在其中。他的诗歌语言像这条街一样,没有丝绸般的华丽,没有外来语,这首《高富路118号》,讲述一个无奈的城市客居者内心的抗争,直观、正确的表述让该诗像质地坚实的一块土布,耐看、耐磨,关键是诗的主题贴肉、接地气。
读潘新安的诗,让我想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场全国性思潮 。争论的焦点,就是文学是一味“歌德”还是“缺德”的某些极端立场。潘新安有自己的底线,也可以说写作立场。一直以来,潘新安追求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有诘问、疑虑、审视的倾向,厌恶邪恶,渴望真理,热爱道德;作品中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博爱思想是较为明显的人道主义立场。是的,一个优秀的诗人都会用诚实的内心面对善良与邪恶。他的描写与剖析自己精神欲望的诗《做个正常人》就是如此:“做个正常人/ 但这需要用药物维持/醒来,一片罗布麻/睡去,一片舒必利/”……有了一个正常的标题后,全诗罗列的事都非正常。这是一首反讽诗,有一股狠劲。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可忴、可悲,在这首诗中,一句一句剥给了你看。让读者一起痛,一起像标题一样渴望着。诗反正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非正常”,什么是“无奈”,什么是“可悲”。潘新安一直在写最底层生活,在诗中自揭伤疤,在诗中和自己较劲。我觉得这样的诗,像诗,也对得起良心。
人到中年后,潘新安也不例外,他也开始了用经验写作。近年来他写了许多“往事”,如《罱泥人》《父亲的杂物间》《掩护》《轮船码头》等等,这些诗以其说是在回忆,其实也是在借往事展开自己对过往的反思;先来看看他的《父亲的杂物间》。
我一直很讨厌我父亲
把别人没用了扔掉的东西,捡回来
一块泡沫,一截钢筋,一枚铁钉
他什么都不舍得
甚至于一张瓦片,半块烂砖头
父亲的杂物间,堆满了
各种各样没用的东西。让我觉得丢脸
但是后来,每当我遇到问题
只要去父亲的杂物间里找
总能找到有用的:
一小片铁皮,一截塑料管
钉子或者绳子。
生活不会总是完美,因为磨损的细节太多了
而我们也从不会去想
我们丢掉了什么
有一些东西那么眼熟,是我曾经扔掉
不知什么时候
父亲把它们又捡了回来
——《父亲的杂物间》
《父亲的杂物间》可以说这是一首标准的经验之作。该诗用父亲捡杂物的细节入手,展开了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全方位的审视。诗中表达了两层意思,即勤俭惯了的父辈们,捡回了许多看似无用,其实都会有用的物件;第二层意思就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也是该诗出彩之处;“而我们也从不会去想/我们丢掉了什么”。这两句诗把诗中的事物,人生经验拉上更高的平台来探讨。
人性与良心是他重要的创作主题,这首《慈悲》也显示出潘新安诗歌温和的一面:“雨水持续的击打/那棕榈,把它最低处/最宽大的一片叶子弯了下来//一只母鸡在叶子下避雨/一条狗在叶子下避雨/我,在叶子下避雨//即便它如此强韧的叶柄/也不停地发抖:在我们头顶的位置/撑住了//如果你不曾历经风雨/你就不会明白,那低垂的湿润和光/就是一种慈悲//现在,你再看着我/你眼睛里转动着的/正是那样的湿润和光//”。该诗用白描的手法,细致地描述了一只母鸡、一条狗、我,在棕榈叶子下避雨的过程,我心存被疪护的感激中,觉悟了慈悲心的真理。该诗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事实,只要心存慈悲,“慈悲”就无所不在,哪怕是一片棕榈叶子也可以是有“慈悲”的。这首诗没有复杂的过程、而是按照“本来如此”的面目再现生活,这也是标准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探索短诗创作,是潘新安近年来有意的尝试,这些诗有浓缩的精华的意味。他的《杂草的命运》《站台》《杉树》《雨水》《 读吉尔伯特的诗》《命名》《入秋》《诗仅仅是诗》等短诗都值得一读。这些小诗都在十行以内,但内涵是沉重的话题。
对穷人来说
忍受,就是一种治疗。
我的疼痛史就是我的成长史,我的经历就是我的病历
每天伴随我醒来,伴随我走路
——《疼痛科》
过了五十岁
才觉得自己渐渐有了一种资格:
说,相信我。
但是对着镜子,这句话却变成了
原谅我。
——《原谅我》
一场集体的凋谢
我独自,踏上梅枝黑漆漆的小径
今夜过后
浔阳楼上,再无题诗人
——《雪夜》
这三首小诗都是潘新安的近作,在刚进入天命之年写下这样的诗,从三首诗的标题就可以看出疼痛、原谅、寒冷的场境。“疼痛史就是我的成长史”。“过了五十岁,相信我变成了原谅我”。“浔阳楼上,再无题诗人”。诗中的疼痛史不是个人的成长史,诗中的原谅我也不是个人的感受,“浔阳楼上,再无题诗人”隐喻当代诗人的某种使命感“凋谢”。他的短诗直观、精确,驾驭语言的能力张弛有度;反思、直击现状是潘新安诗歌的主要特点,在题材的选择上坚守自己的尺度,力求诗的痛感与力量。潘新安的诗给我总体的感受是,能直击现实生活本质,对人性的剖析有血有肉、更有疼痛感,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