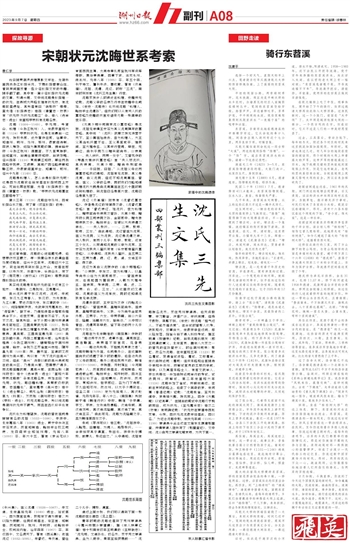沈建平
选择一个好天气,星期天的早上六点,笔者骑自行车从德清乾元大桥的西面桥堍往南,上了高高的东苕溪大坝。
平坦的坝面公路,两旁绿树草坪,花木扶疏。坝区内是平畴沃野的水乡农村,白墙黑瓦的村庄人家掩荫在绿树丛中。宽阔的东苕溪货船穿梭,船笛声声,岸边垂柳吐芽,芳草护堤,平平缓缓的水流,使你很难想象得到汛期里洪水“一夜高于屋”的咆哮和凶猛。
东苕溪,自南而北地在德清县的中部横穿而过,它从余杭的奉口入境,到洛舍出境入湖州有近十七公里,两岸良田万顷,村镇密集。
从乾元镇往南到余杭这一段古称“大溪”,两边的堤坝俗称“险塘”。一个“险”字,道出东苕溪洪水的凶险,请看一下这些记录吧:
清道光三年(1823)3—5月,东苕溪险塘德清段坍塌,大陡门决口,水深四五尺,房倒田淹。
清光绪十五年(1889)6月,德清连雨,险塘数处坍塌,稻田尽淹。
民国二十年(1931)7月,德清降雨411.4毫米,东苕溪险塘倒塌,狂水入注,房屋、牲畜损失严重。
几千年来,东苕溪水灾频繁,以上的这些记录只不过是一鳞半爪而已。
过五闸村时,一辆白色的动车从头顶的高架桥上飞驰而过,“隆隆”地震得脚下的大堤都在抖动,不一会,便到了塘泾村。古时,塘泾是一个集镇,流经镇区的街河西接下渚湖,东连苕溪。在元、明、清时期,这里商贾云集,小镇有九车十三当,辉煌一时。清道光《武康县志》记载:“塘泾,夹溪列肆,溪水四达,贸易者率以划船至,故无任负之劳”。
每年的清明节,塘泾划龙船,做社戏,热闹异常,当地民谣云:“正清明,赤膊上塘泾,划龙船,看戏文……”
塘泾渡,是一处有着千年历史的官渡,早在唐代,便有津渡的记载。河岸边,一个宽宽的石砌河埠,被踩得光溜溜的河埠石,似乎在向过往的行人述说着以往的那份喧闹。随着现代交通的日益发达,它于2005年的12月份撤渡。
往南穿过杭宁高速公路的高架桥,骑上古“张公堤”。清乾隆《武康县志》记载有:“险塘者,通邑水道之城郭也,塘亘十余里,其最险者约二里许,曰张公堤”。
路旁有亭,一石碑矗立于亭内,碑额上题有“重筑险塘张公堤记”。碑文记叙:明嘉靖五年(1526)武康知县张宪率乡民在此地修筑加固堤塘,号称张公堤。明万历年间(1573—1619),武康知县梅一科在张公堤砌石护岸,并在迎水坡修筑一座石栏龙。在随后的两三百年里,张公堤曾多次被洪水冲毁,又多次修复,到了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武康知县徐云笈对大堤及石栏龙捐廉大修,植树固堤,并建亭立碑。
这座至今尚存的石栏龙,在汛期里还在发挥着它的防洪功能,它是古人的治水创举。当洪水流经转弯的险塘时,探向河心尖尖的石栏龙分流水势,减轻洪水对堤塘的冲刷,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过了张公堤,已看得见前面不远处的湘溪大闸了。湘溪港发源于上柏西部山区,早年因外地移民上游开荒种植,下泄的泥沙导致河床淤塞,历史上曾多次疏浚,最近一次是1977年底,全县三万余民工开赴湘溪港,拓浚上柏经下柏至三合出口处的下游河道,并于1978年初完工。
再往南,禺溪出矣。禺溪流经上杨村,这一带古迹、故事众多。昔春秋著名谋士计然曾隐居于此,南宋时期,和王杨存中(1101—1166)病故后墓葬也在这里,故此地有计筹山、杨坟等地名。周边还有升玄观、资福寺、望仙桥、登云桥、仙人碑、棋盘石、龙虎碑等遗迹。
高大的北窑坞大桥横跨东苕溪,桥的东面是原余杭县的奉口镇,一桥连两县。过桥,沿苕溪往北约四里出余杭,再四里,到“上杨湾村”的“清溪禅寺”。清溪禅寺傍着大堤,面朝东苕溪,自清代以来,在每年的清明节,乡民们抬着戴老爷的神像在大坝上巡游,名曰“踏险塘”。千人万脚,来来回回,将去冬新筑的塘堤踏实,以御洪水。
从乾元大桥的西端往南绕了一大圈后,来到大桥的东端,时间已近中午,宽阔的乾水湾就在面前。英溪河从这里出口与东苕溪汇合后,分支出两路:一路经德清大闸往东,一路过德清大桥往北。
旧时,往北是千港百汊的小河道,排水不畅,积涝成灾。1958—1960年,近万余民工开挖导流港,使千百年来奔腾的东苕溪洪水,向北泄入太湖。在以前的老大闸上有一幅对联:“东苕溪危害数千载,开导流造福万万年”。导流港开挖后,涝能排,旱能灌,使两岸的农田真正做到旱涝保收。
在乾元镇街上吃了中饭,稍事休息,便开始了下午的骑行。往西过德清大桥再向北转入大桥西路,过渔民新村,过一个小陡门,前面是“太平坝”了。太平坝是城西包围大坝的一部分,一个很吉利的名字,但在旧时,它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罢了。
过去,工具落后,劳动力低下,每年的冬天,附近各个村庄的村民来这里挑泥加固加高堤坝。年轻时,笔者也来过几次,有几年分的地段在前面的联谊坝。那个时候的大坝上种着高大的芦苇,这种芦苇的植枝高达三四米,地下纵横交错的茎块能起到固堤保土作用。但是它也有缺点,老死的茎块易招来白蚁,白蚁在堤坝上筑巢又影响大坝的安全,所以后来全部砍伐了。
老联谊闸遗址还在,1961年的汛期,闸门两边的堤塘出现管涌,后又溃堤,滔滔的洪水冲向坝区的村庄农田。当抛草包、抛石都无济于事时,村民们划来了自家的小木船,载泥后沉船堵缺口。那天,共有十六条木船沉在这个坝堤的下面,“舍小家,保大家”,这是一种壮举。
老联谊闸对着东岸那棵四季苍翠的千年古柏,该古柏人称“枯柏树”,相传它曾几度枯荣。此地原先有“枯柏树渡”,如今已建起了高大的“枯柏树大桥”,连接着东西大堤。
过桥往北骑行约三里,到了方山脚下的青山坞村,与青山坞相邻的北面是幸福村的太堡堂,建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德武桥”,座落于导流港大坝东三十米的古河道上。当年为保护古桥,导流港开挖时在这里绕了个弯。
德武桥为单孔石拱桥,全长31米,孔跨11.07米,桥下的河道是1958年德清、武康两县合并前的分界线,桥两边金刚墙上的桥联,向过往的行人述说着桥所在的地理方位,和这一带的山水自然风光。且看南联:“叠浪南来,千万脉源从天目。扬帆北去,八十里路达菰城”。北联:“柳暗花明,掩映一堂名太堡。山重水复,弯环十里到清溪”。
再往北四里,发源于莫干山的阜溪自这里出口。阜溪在郭肇村一带有古代的窑址,是“德清瓷”的又一处发源地。这些窑的历史可追溯至商周,历经汉、六朝,直至唐宋。长安、成年坞、丁家浜、郭林桥、三桥林场等窑址,在阜溪沿岸密集地分布着。这里水路交通方便,出阜溪向北可到太湖,红红的窑火曾燃烧了上千年。
过了洛舍大闸,洛舍镇已不远了,洛舍镇是德清县的一个北部水乡重镇,面积达0.671平方千米的洛舍漾傍小镇、临湖州。明顾应祥在他的《东林山新建远眺亭记》里,说洛舍漾“风帆来往,菰蒲交映”。在砂村境内,古有“下潮渡”。戈亭诗派诗人蔡岫青的《重九题下潮渡》云:“侧身天地一儒巾,破浪乘风恨未能。输与下潮溪口渡,载他多少往来人。”
回转,坐在“枯柏树大桥”的边上休息。脚下,东苕溪的河水正浩浩荡荡地向北流去。东苕溪,是德清县的一部水利史,你流过远古时代,防风王曾经在这一带治理洪水,在民间,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你流过封建王朝时代,在每年的清明节,沿岸的乡民们都要举行踏险塘仪式,那是对你放荡不羁的无奈与臣服,溃坝决堤时那一阵阵揪心的报警锣声,印在了古渡口一代代船工的记忆里。你流过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代,那时,两岸的民众万众一心,疏浚筑坝,让你服服帖帖地沿着人们所指引的路走,为两岸的百姓造福。
日月如梭,斗换星移,你流到了今天这个国强民富的新时代。如今巍巍的大堤,伏波安澜,淼淼的苕水,波澜不惊。清丽的苕溪,移步异景,美丽的水乡,如诗如画,骑行在这绿色的滨水大道,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这时,红日慢慢地西沉,晚霞满天,河岸边的那棵千年古柏正见证着眼前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