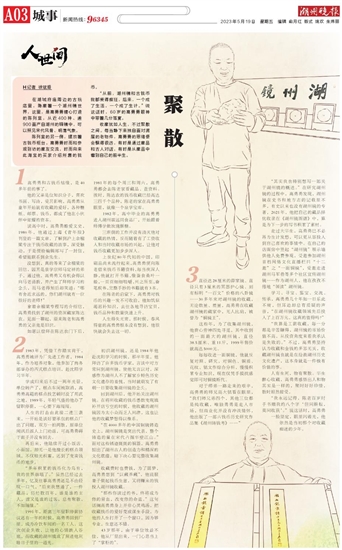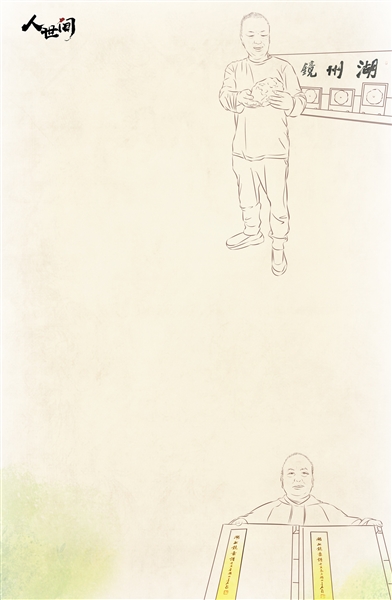H记者 徐斌姬
在湖城府庙周边的古玩店里,隐藏着一个湖州镜世界,这里,是高勇勇精心打造的陈列室,从近400种、逾900面产自湖州的铜镜中,可以照见宋代风骨、明清气象。
陈列室的另一侧,摆放着古钱币柜台。高勇勇时而和参观到访的藏友交流,时而向来此淘宝的买家介绍所售的钱币。
“从前,湖州镜和古钱币我都爱得痴狂,后来,一个成了生活,一个成了生计。”说这话时,60岁的高勇勇眼神中带着几分落寞。
收藏犹如人生,不过聚散之间。每当静下来独自面对满屋的老物件,高勇勇的思绪便会飘得很远,有时是通过藏品和古人对话,有时是从藏品中看到自己的前半生。
1
高勇勇和古钱币结缘,是40多年前的事了。
他的父亲是位知识分子,喜欢书画、写诗,受其影响,高勇勇从童年开始就有收藏的爱好,各种糖纸、邮票、钱币,都成了他在小伙伴中炫耀的资本。
读高中时,高勇勇酷爱文史,1980年,他通过上海《青年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了解到沪上余榴梁专注于钱币收藏的故事,深受触动,于是便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希望能联系到余先生。
没想到,真的等来了余榴梁的回信,因其是泉学宗师马定祥的弟子,通过他,高勇勇又有机会得以向马老请教,并产生了拜师学习的念头,而马老得知后却笑道:“哪有舍近求远的,你们湖州就有一位很好的老师!”
拿着余榴梁专程写的介绍信,高勇勇找到了湖州的资深藏家陈达农。见面一聊起,原来陈老和高勇勇的父亲竟是旧识。
如愿以偿拜在陈达农门下后,1981年的每个周三和周六,高勇勇都会去陈老家看藏品、查资料。彼时,陈达农的钱币收藏已经高达三四千个品种,陈老的家在高勇勇眼里,就像一个泉学宝库。
1982年,高中毕业的高勇勇进入湖州震远同食品厂,开始跟着师傅学做玫瑰酥糖。
三班倒的工作并没有浇灭他对收藏的热情,反而随着有了工资收入和当时收藏市场的兴起,让他对钱币收藏更加步步深入。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印刷品尚未流行起来,高勇勇便向陈老借来钱币书籍资料,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打开书籍,像蚕食桑叶一般,一页页细细咀嚼,兴之所至,奋笔疾书,完整手抄的书籍就有3本。
在陈老的启蒙下,高勇勇对钱币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他如饥似渴恶补知识,去往各地寻访宝贝,钱币品种和数量快速上升。
人生得失无常,那时候,春风得意的高勇勇根本没有想到,他很快就会失去这一切。
2
1983年,凭借工作踏实肯干,高勇勇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1984年,作为培养对象,他参加了商务部举办的西式糕点培训,赴沈阳学习半年。
学成归来后不过一两年光景,单位转产了,糕点车间被取消,高勇勇高超的糕点技艺顿时没了用武之地,1989年,年轻气盛的他办了留职停薪,一心要下海闯闯。
人生的打击由此接二连三袭来,一开始是谈好要承包的糕点厂出了问题,双方一拍两散,原单位闻讯后派人上门劝返,可高勇勇碍于面子并没有回去。
再后来,他陆续开过小饭店、小面馆,却无一是他擅长的糕点领域,不仅赔光积蓄,还到了变卖钱币的地步。
“多年积累的钱币化为乌有,我的世界崩塌了。”虽然已经过去多年,忆及往事高勇勇还是不由轻叹一口气,“后来我想通了,一件藏品,历经数百年,谁是谁的主人,谁又是谁的过客,总有聚散,不如随缘。”
1991年,距离三年留职停薪协议还有一年的时候,高勇勇回到厂里,成为冷饮车间的一名工人。这次创业失败,让他的心情跌入谷底,而收藏的湖州镜成了照进他灰暗日子里的一道光。
初识湖州镜,还是1984年他赴沈阳学习的时候,那半年里,他拜访了许多钱币学家,言谈中对方常问到湖州镜,使他无言以对,深感作为湖州人不了解家乡特色历史文化遗存的羞愧,当时就萌发了有朝一日要收集湖州镜的念头。
回到湖州后,他开始关注湖州镜。在将所收藏的钱币悉数变现填补开店亏空的时候,他收藏的湖州镜因为太小众而乏人问津,这也让他的收藏梦想得以维系。
“在4000多年的中国铜镜铸造史上,湖州铜镜是突出代表,整个铸造的量在宋代占据半壁江山。”面对这些锈迹斑斑的铜器,高勇勇掂出了湖州古人的创造力和精深的文化底蕴,暗下决心要完整收集湖州镜。
收藏费时也费钱,为了圆梦,高勇勇想到“以藏养藏”,他说服妻子做起钱币生意,又将赚来的钱投入湖州镜收藏。
“那些你读过的书,终将成为你的骨血,改变你的命运。”这句话搁高勇勇身上并非心灵鸡汤,把收藏钱币的爱好变成谋生手段,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个窗口,因为够专业,生意还不错。
43岁那年,由于单位效益不佳,他从厂里出来,一门心思当上了“掌柜的”。
3
直径达28厘米的薛家镜、直径只有3厘米的冥器护心镜、刻有标明“一百文”价格的八卦镜……30多年来对湖州镜的收藏,无论数量、质量,高勇勇在收藏湖州镜的藏家中,无人比肩,被誉为“铜镜王”。
这些年,为了收集湖州镜,他费心劳神四处寻觅,其中收到的一面最大的湖州镜,直径38.5厘米、重11斤,1999年售价就高达5000元。
每每收进一面铜镜,他就反复对照、研究,对铜色、铜质、花纹、铭文作综合分析,慢慢积累专业知识,现在仅凭手摸找感觉即可对铜镜断代。
对于师弟一路走来的艰辛,高勇勇的师兄高大铭看在眼里,“我们师兄弟四个,其他三位都是纯收藏,唯独勇勇是走入市场,但商业化并没有冲淡情怀,他出版了一部古钱币历史研究作品集《湖州铸钱考》……”
“其实我也特别想写一部关于湖州镜的概述。”在研究湖州镜的过程中,高勇勇发现,湖州镜在史书和地方志的记载里不多,有史以来也没有湖州镜的专著,2021年,他把自己的藏品择优收录在《湖州镜图谱》中,算是为下一步的写书积累了素材。
走过大半生,高勇勇已不必再为生计发愁,可以更从容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在自己的店面房中竖起“湖州镜”展示墙供他人免费参观,受邀参加湖州首档网络文化直播栏目“十二邀”之“一面铜镜”,受邀走进湖州马军巷等多个社区宣传湖州镜……作为湖州人,他在孜孜不倦地“领读”湖州镜。
学习、寻宝、鉴宝、交流、传承,高勇勇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但耳边却总有质疑的声音,“在湖州镜收藏领域先后投入了上百万元,这真的值得吗?”
“我算是工薪收藏,每一分都是辛苦赚得,湖州镜的市场价值不高,从投资角度来看我承认是失败的。”不过,高勇勇坚持认为收藏和金钱的多寡无关,收藏湖州镜也就是在抢救湖州历史文化遗产,这本身就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
人有生死,物有聚散。半生醉心收藏,高勇勇感悟出人和物其实是一样的,聚时好好珍惜,散时坦然接受。
“我永远记得,陈老百岁时手书赠我的八个字‘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说这话时,高勇勇一脸坚定,眼里闪着光,他依然是当初那个对收藏痴迷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