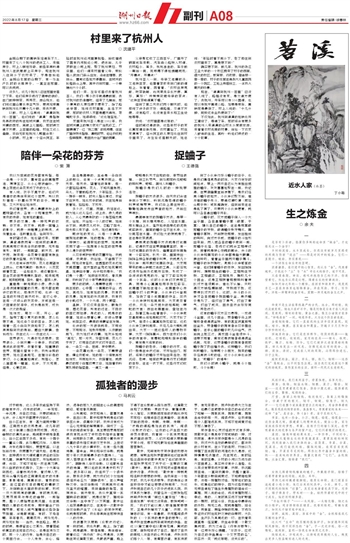○ 马利云
对于锻炼,这么多年我能坚持下来的唯有步行。行走的时候,一半观览,一半沉浸,与自己对话。只要时间体力允许,什么地方我都愿步行到达。
出小区往东,有一甚为阔朗安静之园,江南雨水的滋养浸润,没几年时间,这个新建公园已绿树成荫。河边,垂柳依依清风徐徐,晚间散步锻炼者甚众。出小区往西不多远,有另一个园子——霅溪公园,此处霓虹闪烁,人烟市肆,与东边园子相比,更显繁盛。以往饭后行走,我更喜欢广阔天地,总是往东,在种满乔木大道或灌木被径的石阶兜几圈,神清气爽地回家,开始晚间功课。近日,不知不觉地一改往常习惯,我从幽寂的东边园子,又折一个大弯绕到西边。沿着市河行走,看对岸人家,那马头墙风格的江南建筑在夜的光影里,影影绰绰,高高低低。看桥的轮廓,在红蓝的炫目的霓虹的镶嵌之下,与倒映在水里的桥的轮廓,构成一只大而明亮的眼睛。有时微风起,又晃荡起来与岸边的垂柳,一起摇晃,整个人便摇晃在微风里。也在跳舞的人群的边缘疾走,脚步暗合广场舞节奏,感觉人间气蕴藉在这些杂沓节拍里,浮艳歌词里。有时,不免自嘲,年年春风,朝朝花开;何处无月,何处无松柏……当然,走在路上,更多的时候,是停留在心之某处。想着若能够真正的注视自己内心,总是在独处之时。而一个人的行走,恰是与自己的一个美丽约会。一个人走走,会心、释然,滤净的那久久的搁在心头的潮湿和郁闷,感觉春风拂面。
众所周知,作家和诗人,都喜欢漫步。自古以来,散步和思考就是他们的亲密伙伴。读高中之时,我并没有成为一名心无旁骛的解题高手,倒成了一名十足的阅读爱好者。其主要因素是那时候我有机会成了学校图书馆学生管理员,利用职务之便,阅读那个藏书并不丰富的读书馆仅有的文艺书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镇学校,也有一些外国诗集,普希金、拜伦和华兹华斯,就是那个年代我接触最多的外国诗人。“任何人若想在外漫步,必须孤独如一朵云”,湖畔诗人华兹华斯,以他歌咏自然的诗篇,更以他的孤独漫步吸引了我。很多年以后,我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根本没多想,就为我们这个女性阅读组织命名为“湖畔读书”。在众声喧哗之中,华兹华斯说“我常离开这沸反盈天的喧嚣,来到偏僻的角落,自娱独乐,悄然旁足,去纵步直穿一孤星映姿的湖面”,就是这样了。据说华兹华斯一生中走了18万英里。散步让人他获得最佳状态,在其中一次散步中华兹华斯产生了《水仙》的写作灵感。也就是那时候,我也非常向往那种独自一人的行走。
我很喜欢狄更斯《伦敦夜行记》。有一段时间,我也失眠。晚上,除了翻书,就是翻身。思绪奔腾,身体倦怠。跟着这位“独行侠”作心灵漫游。狄更斯在写这篇散文前,失眠很严重,晚上不得不在伦敦街头四处游荡。这篇散文体现了狄更斯一贯的才华,意蕴深厚,令人难忘。狄更斯把可怕的夜晚比作无家可归!他强迫自己在黑暗中,在绵绵不断的雨中,走啊,走啊,走啊……“夜晚的道路是如此的孤独”,阅读《伦敦夜行记》,让我的心产生巨大的冲荡与悲悯。我看到一个孤独灵魂在黑夜里的游荡,人们只知道狄更斯善于写小说,却不知无眠如他在黑暗里的苦苦挣扎。
散步,无疑有助于写作者的构思与遐想。爱默生和梭罗都提到他们在新英格兰森林中的散步激发了他们的写作,包括梭罗完成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散步》。康德、贝多芬和尼采都是痴迷的步行者。卢梭说:“散步有一种刺激和活跃我思想的作用。当我呆在一个地方时,我几乎无法思考;我的身体必须在移动中才能让思想运转起来”。为这卢梭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送进孤儿院,我对其极为嫌恶。我曾经与一位教授抬杠质疑卢梭所谓“顺应儿童本性”“身心自由发展”学说之没来由,教授呵呵一笑,“我们不能以常人思维揣度思想家。正是卢梭解放了儿童”。然而,我嫌恶依旧。有一年暑假,我完整阅读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思考》,这是卢梭在世最后两年间写就的作品。在这10篇文章中他以散诗笔调,真诚的态度,剖析和评述了自己,描述了自然的美和人与自然的心灵沟通。卢梭与我们每个人一样,有痛苦彷徨,有孤独寂寥,有无奈悲伤。而卢梭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最终在遐想中与自己的命运达成了和解——拥抱孤独,拥抱疼痛,拥抱生命中的每一天。阅读卢梭,让我领悟每个人都难逃孤独,不知不觉间竟对他不那么嫌恶了。
写作者与心灵对话的方式有多种,而散步至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对我而言,漫步与写作都是令人沉浸的活动。我对户外活动的最早记忆,都与我的乡村有关,在乡下的桑树、竹林以及种植了豆类蔬菜的河滩边长久漫游。这种情景无法描述,风在耳边,有时轻柔、有时狂暴,乡村的小河以及远处的六百亩漾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渔船,也从来没有带来远方故事。然而,我沉醉而自适,一直到我高中,我整个童年、少年都在乡野田间度过,不知疲倦地探索。与每一株植物对话,观察他们的生长,收集他们的种子,因为这些我早已无师自通地了悟生长是植物的宿命这一真理,而人类的命运,远没有植物那么幸运,是的,人有时其实远不如旷野里的一棵树。时至今日,我生命中最亲近的外物,别无二选,那就是植物。旧仓库、养蚕室、轰隆作响的机埠,不远处象征我们村庄庇护之神的白果树,大队部、生产队及其周边的一切,在我看来简直是一座宝藏。我生命中第一个散文集问世,我为之命名《行走与思考》。有一位师长好心提醒,“女孩子,应该为自己的作品集命一个文艺范的名”。我率然一笑“就这样吧,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