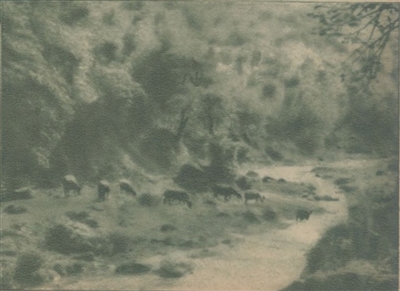朱炜
德清莫干山,既为山之总称,主峰塔山,门户炮台山,其附近之名胜,则东段有高峰山、天池山,西段有天泉山、葛岭,南段有石峤山、石颐山、铜官山、黄回山,北段有横岭、龙池山。
一
横岭,土音黄岭,是莫干山北段一支东西走向的山梁,莫干山避暑区西北址即划到横岭,因多竹林,有“竹林海洋的一角”之称。横岭东麓即横岭村,与范家坞、莫家坎、福水村、溪北村、斗将坞、后洪村等,昔同属归安县二百十六庄、二百十七庄,为吴兴、德清、安吉三县区交界处,今归德清县莫干山镇南路村。深山冷岙交通不便,加山冲田贫瘠,村民靠毛竹山上的毛竹以及砍伐运输毛竹为生。毛竹一年大量发笋长竹,一年生鞭换叶,交替进行,每两年为一周期,称大小年竹。旧时大年留笋养竹,小年伐竹劈山。自家山林中的每一竿竹,就像家里的每一只鸡,村民一眼就辨识出来。他们会在竹竿上写上姓氏,以便分辨挨得很近的各家竹林。同时,同一年生长的竹子会写有一样的数字,次年便递增,用的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老底子的苏州码子,由算筹演变而来,不知何时传入这里。于是到砍伐时就知道该砍掉哪些好多年的老竹子。这种标识会用特殊的油墨,雨雪都不会化,也会雇来专门的抹字人:姓氏和数字都是用手指抹上去的,他们抹得又快又好。
莫干山原住民多同姓聚族而居,昔有宗谱放在祠堂里,惜未能保存。文字失载,老人们喃喃不清的叙述里有徽州和苏州,有避战乱,亦有哀毁荣喜。潜伏在山村的百年前甚至上百年的记忆,一直在等待一个契机,等待被召唤,然后化为一瞬的恍然。据何世旺老人家堂屋供桌木匣中所藏故纸,祖籍安庆怀宁县的何氏,自清光绪年间迁来,有五言辈分诗:“万仕贵觉显,伯碧仲大应。嘉振守启文,伟恩光国令。希世承宏广,英华润泽长,贤良逢道泰,俊烈际时昌。为善昭明哲,存仁理法章。修齐端立本,平治颂中邦。”作为最早来莫干山的第一批安徽人后代,乡音不改,取名不数典忘祖,何世旺是世字辈,其孙何宏亮正是按辈分诗取的名。洗帚曾是每个家庭灶台上的必备之物,清洗镬子、锅子又干净又不伤锅,一把能用大半年,关键价廉物美。莫干山避暑地兴起前,莫干山周边没有人会扎洗帚,后横岭一带迁来不少安徽安庆人,因没有田地可耕,无奈以上毛竹山挖竹根扎洗帚为营生。竹根长在竹蒲头上,不能挖断主根,要用开山锄把整个竹蒲头连根挖起,挖上一天最多也只能挖七八个,相当费力费时。挖完竹蒲头,要把竹根砍下来,捆好背回家,铺在家门口晒。等表皮晒干,换用大木槌子敲去外壳,一把木槌子有十多斤重,要连续不断敲。紧接着还要再经一道晒的工序,等到竹根发白方能扎洗帚。扎洗帚的师傅会熟练地拣出若干长竹根和短竹根,用毛笋壳拦腰裹紧,再将长竹根翻下来裹在外面,用铁丝扎紧,然后用剪刀剪齐,最后倒过来在中心敲入木塞,一个称手的洗帚才算完工,其中辛苦只有自知。
二
横岭水,是埭溪上源5条支流之一,溪沟里有很多大溪石、大而圆的鹅卵石,很漂亮很光洁。作家周瘦鹃1928年7月曾游横岭一带,在游记中写道:“至斗将坞,修篁曲水,已渐渐引人入胜”“过……后洪、溪北诸地,迢遥数十里,一溪潆洄,未尝中断。每隔百余武,必有巨石错落水中,不一其状,水自乱石间下泻,作声甚厉,汤汤然,吰吰然,渊渊然,如磬,如钟,如鼓,无不肖也。一路水光潋滟,水声不绝,悦目赏心,于斯为极。”“已而至莫家坑……自莫家口循溪而进,水光接舆,山翠扑人。”斗将坞,又名对将坞,今作斗蒋坞,半山里古道,东起对将坞,西至天泉山,年长月久,碎石已被鞋底磨滑,而斗将坞悬崖峭壁上开凿修造的一条全长1100余米的灌溉水渠,亦可称“红旗渠”。莫家坑,旧称莫家磡,今作莫家坎,村名就刻在一块2米多长、1米多宽的溪石上,村民们当年为迎接这块失而复得的大石头,还放起了鞭炮。
《莫干山指南》载,横岭,“猎者咸集焉”。莫干山避暑西人酷爱打猎,杭州蕙兰中学校长葛烈腾在回忆录《人间世》里就描述了到莫干山的狩猎活动,拓宽了我们对莫干山地理区域的想象。即便是在生活中大型野生动物已经难觅的现代,还有莫家坎青年俞孝良于1999年在范家坞四面山上,发现山顶上有一头黑色的岩羊,并送往杭州动物园饲养。横岭生态园负责人赵雪峰则称,2006年在横岭茶场发现一头四不像——鬣羚。近年,在横岭一带,常能遇见拱番薯地觅食的野猪。
现在的人最为称道的还是莫干黄芽的传奇,这是唯一以莫干山命名的区域知名农产品。作为莫干黄芽统一工艺时首个试制地和主要产地,横岭大山顶有一棵古茶树,即莫干黄芽横岭一号种的母树。若说伐竹、扎帚是技,那么制茶不仅仅是技,更是道,是手艺人劳作、磨炼、继承与发扬的过程。横岭海拔高,土质好,常年云雾笼罩,空气清新,非常适宜茶树生长,加之有以汪祥珍为代表的制茶师数十年的坚守,自然和手艺与追求连到一块,便到了一个高的、类乎于哲学的境界,令出自横岭的莫干黄芽品质优异。
三
莫干山一带山水之美,以福水为第一,游莫干山而不游福水,则犹入宝山而空手返也。
福水村,古名上阳村,因西南有高山名阳山,今有地名阳山庵。民间故事,在明代前,有看风水的先生从相邻的安吉县一路走来,只见这里的地势平坦,四面青山环绕,绿树成荫,山道旁的两股溪水一左一右相伴并流,汇集在村口一块宽广的大岩石之上,如碧绿的珠宝,随后湍湍向下游流去,不时溅起一朵朵浪花。该先生对村中长者言,这村庄有如此风物,可改一改名,但具体改何名则没有说。星移斗转,朱元璋的大军翻山越岭至此休整,士兵饮罢此水情不自禁连呼:“好喝!好喝!真是一溪福水!”带队将领就在溪坑边的沙滩上用木棒写上了“福水”两个字。每遇旱季,邻村的小溪干涸了,福水村的小溪仍涓涓细流滋养山村,真应了福水其名。
莫干山避暑西人往福水村者多从芦花荡下行,经花坑、沈家岭即到。诗人柳亚子1928年因游碧坞之龙潭,遂至福水村,有诗纪之,云:“福水源头阔。”庶几同时,作家周瘦鹃游福水村,闻福水之名,已觉此吉祥名字,大足动听。观农家安居力田,怡然自足,鸡犬桑麻,亦一一似含乐意,一路水声咽石,似作欢迎之辞,已而见短瀑当前,如白虹倒映,厥态奇美,声宏而清,则如琵琶疾奏,作《十面埋伏》之曲。周瘦鹃拄杖截流而渡,讵中有一石,滑不留足,一足遂入水,乃去袜履,解衣磅礴,手执蕉扇,侧首作听水状。同行的友人张珍侯为之摄“福水濯足图”,刊于《上海画报》。1930年《中华》杂志上还刊过《福水》风景照。
然而,避暑人士毕竟是过客,风光故事的背后,是早期村民生活艰苦异常。从福水村到埭溪镇上有45里路,到三桥埠有35里路,一二百斤山货背出去,换几升米回来,一个来回就近百里,每次出门都只能是起早摸黑。因此,有一句民谚流传甚广:“出门鸡叫,进门鬼叫。日里跑路呒功夫,夜里跑路老虎拖。”但随着山乡巨变,今非昔比,不变的是福水长流。
四
当地人达福水村,会走后洪村的大木桥。桥旁风景清美,桥跨溪涧,竖木为桥脚,外裹以藤,内实砂石,系溪桥中胜迹。清乾隆时大堰桥(六洞桥)构造法与此相同,当木桥脚尽改石柱,惟此桥可窥古时建筑之一斑。
青山绿水亦有幸埋忠骨。抗战期间后洪村山边曾埋百余名抗日阵亡将士的忠骸。据王金庆老人回忆:“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讲,当地有一座山长满了老松树,属庙产,都是很粗的老松树,可能上百年没有人动过。得知抗日将士要砍伐松树备棺材上前线,寺里和百姓纷纷支持。于是,整片山林都被砍下来做棺材,附近的木匠都来做棺材了,场面极其感人。”1940年6月,在高峰战役中阵亡的抗日官兵被运往后洪,并葬于此。1945年8月有两名新四军战士在范家坞就义,遗骸掩埋在范家坞1号屋东北毛竹林中。忠魂绕白云,成为这绿水青山间的旋律之一。
苏轼有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初读只在字面意思,横岭侧峰,山中之人看到的是岭,山外之人看到是峰。多年以后,当体内的群山日益寥廓,这种理解最大限度地呈现在笔者进入莫干山世界的文字路径中。温暖的,即是熟悉的,就是家园,无论百年前与今天;陌生的,抑或无从知晓的,才称为路途与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