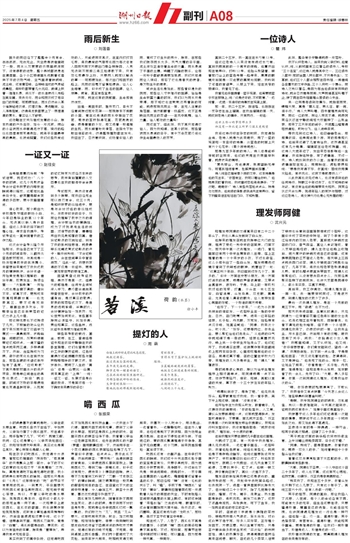○ 瞿炜
直到二十五岁,我一直住在木勺巷12号。
但这位老诗人从来没有走进过木勺巷。直到我搬离前的一个周末的傍晚,他蓦然出现在巷弄口,打听12号。他抬头张望着,顺着那门台上的蓝色号牌一路寻来,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一双迷蒙的高度近视眼。我听到了邻居的言语声,从楼上下来,站在狭窄的楼道口,我看见了他。
我看见他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他弯腰把篮子放在楼梯上,说:“这是送你的,不成敬意。”一边说着,一边把一本油印的诗集放在鸡蛋上面。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刚结婚,也刚刚在一家杂志社当上编辑。在我当编辑的第一天,就收到老诗人的稿件,只有两行,一句话:
这世上伤心的事情那么多
却没有一件比爱上所罗门国王更绝望
我将这诗行印在杂志的封底,我觉得挺合适。老诗人就是为此来谢我,用了一篮的鸡蛋和一本自印的诗集:淡蓝色的封面上只有六个毛笔字:《秦少游诗词选》。
那是九百多年前的诗人。诗人总是能够穿越时空而来,他们的灵魂在云层里穿梭着,就像夜鸟的啁啾。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诗人说自己惟爱秦少游的文字,这本诗集是他的笺注本。“你若有空,我可以唱给你听。”他用微笑盯着我说。我诚惶诚恐地连连摆手:“下次吧,谢谢你!”诗人有些失落地点点头,转身匆匆而去。他佝偻的背影很快消失在巷弄口,留下我瞠目结舌地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此刻,整条巷子安静得就像一片落叶。
我不认识老诗人。后来我向父亲打听,他竟认识,说,从前城里有三位著名的读书人,号称“三个活宝”,这位诗人就是其中之一。三位读书人都穷(那时全国人民也都穷,不只是书生)。文革前,他们三个人都会相聚在图书馆,一起借阅各自喜欢的文学作品,三个人共吃一个馒头。而诗人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每当他读到有共鸣的诗句,就会忽然腾身而起,大声朗诵甚至吟唱不止,惊了同在图书馆里埋头苦读的众书生。
另一位则是每读到动情处,就拍案而哭,嚎啕大哭,真是“莺儿狂。燕儿狂。歌一阕,泪千行。”诗人大声吟唱,图书管理员尚可叱责,而这一位的哭,则让人哭笑不得。就像阿芙洛狄忒在宁静的阅览大厅里种了一丛桃金娘,却来了三只祭祀的鸽子,只把整丛喧腾得枯枝遍地,败叶纷飞,任人徒唤奈何。
等我见到这位诗人,他已垂垂老矣,却痴情依旧。他虽痴迷秦少游,写的却是现代诗。他后来还寄了几首诗给我,浓烈得甚至还有几分艳情。编辑部主任老成持重,说,这诗人大把年纪了,发出来恐怕影响他一生清誉。我将原话转告,写了退稿信。才过一天,诗人就找到我的办公室,当着我的面将退稿信摔在地上,用脚踩住,满脸悲愤地说:“要是我写得不好,你直说!若说我用情太轻佻,有伤风化,这岂不是欺辱我么?”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诗人,也没有读到他的任何诗行。转眼三十年过去了,也不知诗的爱与欲,有没有给他的晚境带来光和热。阿芙洛狄忒只会戏弄、挑逗年轻人的嫉妒与相思,对这位老诗人,连女神大约也是心无所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