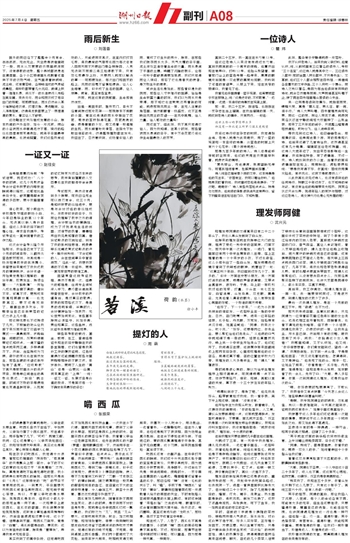○ 张振荣
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吃。父亲在做水果生意,吃西瓜自然不在话下。午饭辰光,父亲如约捧了个西瓜回家,放在桌子上,用手指弹了几下,“咚咚”既脆又甜。我问:红心还是黄心?父亲爽快地回应:红。我和妹妹便欢呼起来。其实这也是莫名其妙,黄心照样也是甜入心肺。
现在孩子们吃西瓜,我觉得十分浪费,看那垃圾桶里的“废弃物”,“取其精华”的只是瓤尖上那一部分,余下的不论红的黄的统统归之于“弃其糟粕”之列。唉,真是有得吃不晓得无得吃的苦。我小时候虽也有吃西瓜的愉悦,但那也只是类似“七月七”这样特定的“吃”的节日才有享用的机会,一到夏天,平日里想天天吃西瓜或者经常吃西瓜,那无疑于痴心妄想。所以,尽管父亲吃的是水果饭,挑拣西瓜是本行,但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完全是一窍不通。一次和妻子上街买西瓜,在瓜农的篰里,我也装模作样地挑挑拣拣,还煞有介事地拿起来弹弹听听,然后自信满满地对妻子说,这个不错。结果拿到家里,用西瓜刀剖开,竟是个“白脯”,连瓜籽都是白的。妻笑我:还以为有祖传的本事,原来是“冒牌货”,弄得我有点无地自容。
其实我到了初高中阶段,已觉得吃西瓜不如挑西瓜有科技含量。一次我在乡下代课,星期天回家闲来无事,便到了父亲的水果店,那时正是西瓜上市的时光,店里买西瓜的顾客络绎不绝。我看着父亲给一位老顾客挑西瓜,他先在装西瓜的大篰(箩筐)里用眼睛扫视一下,然后用手在一个花纹清晰的西瓜表面轻轻地弹了几下,声音似乎很脆。他点点头,表示此瓜不错。然后问顾客:“要开吗?”当得到顾客的首肯后,父亲便把西瓜捧到案板上,操起西瓜刀,等到刀锋一接触瓜皮,似乎还没有用力,便传来卜卜爆裂的回响,使人等不及地看到又听到了“刀割一寸皮裂三寸”的精彩瞬间,随之喷薄而出一股爽鼻的甜香和悦目的血红,在店堂这不大的空间中弥漫着,令人垂涎三尺。顾客十分满意,喜滋滋放进篮子拎回家了。
西瓜有好几种吃法,随着年龄不同而发生变化。很小的时候,是求快而不计较自身形象,那就是让母亲把西瓜切成一瓤一瓤的,我们称之为“叉”,而且“叉头”要大,这样吃起来爽快、煞念。加之吃相不雅,和妹妹抢着吃,非要一块块啃咬到翠皮白肉边缘留下齿痕深深的馋吻方才罢休,觉得这样的滋味才完整、才完美。等到桌面上西瓜告罄,我们两个都闹成了大花脸。后来年岁大起来,吃相就变得文明起来,我喜欢一个人吃半个,用汤匙舀,一边看着书,一边静静地吃。但在外人看来,总归还是脱不了狼狈相,因为动用金属汤匙后,往往会不停地往深处刮,不但把红的、黄的西瓜瓤清理得干干净净,甚至于见白露青。这个习惯,后来阴差阳错地一直延续下来。
吃西瓜还有一份副产品。在母亲打开西瓜的瞬间,我们还十分关注西瓜肚子里的宝宝是否有戏,只要子黑就好。因为把西瓜子积累起来,洗净晒干,炒过后也不失是一种消闲美味。傍晚时分,一家子围坐在靠窗的八仙桌边,嘴里嗑着还留着余温的瓜子,那已经和“啃”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了,叫“嗑”。手底下是“啃西瓜”留下的“精华”,眼睛则扫描着西边那一片满载着火烧云的美丽的天空,不时有航船从百间楼河晶莹的水面上飘过,有时还伴随着“来船松摇”之类的吆喝。眼福好时,还会看到雷阵雨大驾光临,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甚至还有远处的“龙吸水”。那场景,绝对不亚于收看空中电影。
现在成人了、人老了,西瓜也不再是我的喜好,小时候“啃”西瓜的美姿和情景不再涌现,不过,那场面、那情节在思绪中随时可以穿越、可以重温,因为那是一种天真、一种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