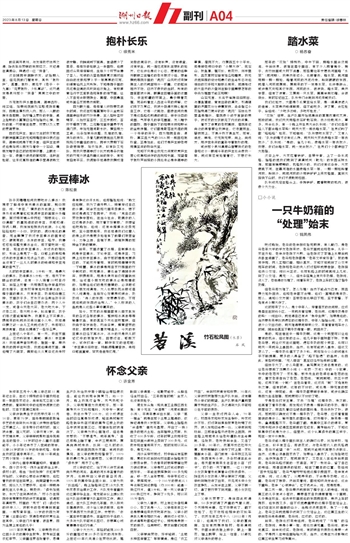○ 许金芳
癸卯年五月十八是父亲己故11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和往年一样回老家纪念,呆呆地兀立在父亲遗像前,看到照片中的他那布满皱纹的脸时,双目不禁潮红起来……
父亲许新贵生于农历甲戊年11月16日,享年79岁。祖母是跟随做裁缝手艺的叔伯到长兴与祖父许寿林结婚的江苏镇江人,日本鬼子打进村时,祖父被杀害,祖父死时,父亲只有3岁。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早早就帮助祖母挑起生活的担子,14岁时已什么重农活都能干,小小年纪尝尽了人世间的艰辛。父亲24岁时与15岁的母亲成婚,母亲生我时正值非常年代,尔后10年间生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父亲内心里非常尊重知识,看重读书,四个孩子无一例外全部供给上学。读村小时,每当“抢收抢种”农忙季节开始时,父亲的心思总会被触动,他拉着我的手站在田埂上,向南望着长兴县城,视线久久不愿移开,他将一种期待寄托在儿子身上,鼓励我:“读书加把劲,长大了住到县城去。”村小办在庭院中有棵黄杨树的许家祠堂里,记得那年清明节,村里的“秀才”们(读过书的识字人),被教书的老师请到祠堂里,一起聚餐祭祖。13岁的我因为写了篇《兰香山记》获得老师的欣赏也坐在其中,父亲在门外看着,很自豪,因为坐席上有他的儿子!
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鼓励我这位回乡务农的高中生报考。报考后正值农忙季节,父亲重活累活抢着干,恳请生产队长给我安排个晒稻谷等轻便农活,能让我利用余隙复习。近一个月,晚上我挑灯备考,天气热蚊子多,父亲用蒲扇为我赶蚊子。那一年高考只分文科和理科,大中专一套试卷,我总分考了335分,这个成绩在当时已经算是好成绩,贴在县城解放路老新华书店对面的高考红榜上我的名字被写在第三位,可惜体检时被淘汰了。父亲虽为我心里难过,但总是安慰我:“不要泄气,明年再考。”自己却晚上睡不着,半夜三更起床,摸黑向县城走去,找到一位儿时的伙伴,一起到医院院长家里,询问我的情况。在父亲的鼓励和督促下,1979年我最终考上平湖师范。父亲对我的“读书梦”用尽了心思。
对父亲的记忆,绕不开从许家滨通向外界的河流,温润的河水丰盈着我的岁月,也映照出父亲的音容笑貌。1975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后,父亲为我“找出路”,晚上摇船到红家土斗大队支书家恳求给谋份工作。大队支书看重我这位高中毕业生,党支部会议上提议我任大队出纳兼管大队畜牧场工作,得以通过。在大队工作的几年里,我人际关系搞得被动,没少给父亲添麻烦,他走东家串西家为我做工作。安慰我:“你一直在学校里读书,在畜牧场干活的人大多与大队干部关系密切,你要真心诚意慢慢与他们沟通。”
父亲个大力大,年轻时能挑200多斤的重担过有20多级石坎的浣东桥。上世纪60年代夹浦公社劳动比武,掘畈田父亲得第一。他勤劳能干、头脑活络全村出名,“三年困难时期”全家人也没有饿肚子。
港北东头角(现夹浦工业园区西北角)有个无主“浮渚墩”(河港包围的小洲),平常年景浮出水面,父亲“第一桶金”就是在那个土墩上掘得的。依稀记得是我8岁那年,父亲晚上摇船去“浮渚墩”借月光垦荒,开出了一块3亩多的肥沃土地,当年播种上芝麻,秋收了400多斤籽,过年时带上我用手拉车拉到宜兴街市上卖到了300多元。这数字现在看起来不大,那时足可以买头牛,是笔大钱。
浣纱溪穿村而过,村中临溪有座粮库,夏收秋收后附近村庄都会摇船来交公粮卖余粮,冬去春来时粮库要雇壮劳力装运粮食。父亲是村上打包运粮的一把好手,一年能在粮库挣到100多元现金,够一家人全年零用。母亲夸奖过父亲,粮库规定,一个150斤的粮包从1号仓库扛到运粮船(约200米)能拿一块红竹爿,值3分钱,有一天父亲拿了300块红竹爿,挣到了9元多,可以买15斤猪肉。
父亲为人善良。村上有位长者和清公公,老了孤身一人,父亲每年年三十总是要请他来我家吃年夜饭。父亲小时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得到过乡邻好人的点滴帮助都铭记于心,特别是贵娘一家的接济,经常唠叨,要求后辈们知恩图报。
父亲崇尚劳动,好学钻研,“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样样精通,是位“农工巧匠”,受到村民肯定和称赞。70年代父亲被村民推荐为生产队长后,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生产队粮油产量明显高于别的生产队,多次得到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的表扬。
父亲一生救过两条人命。70年代,村西朱家和叶家发生争吵,叶家成份不好,打过架后惧怕报复老叶喝了农药,被人发现已命悬一线,父亲赶到现场后,立即准备船只送老叶上医院,并在船上用肥皂水给老叶灌肠与生命赛跑,经抢救,老叶劫后余生,又活了20多年。80年代,改革开放己拉开大幕,敢吃螃蟹的父亲开了村上第一家私营副食小店,店门前有一条平板三孔石桥,桥西有所小学,多条村道在此会合,每天都有南来北往客在小店“打卡”。初冬的一天下着雨,一位11岁的小女孩背着书包撑着伞过桥去读书,一阵狂风小女孩连人带伞掉到了河里,父亲听到响动冲了出来,只见河水中小女孩在挣扎,头发浮在上面,父亲不顾一切,拿了根竹竿下到河里,把小女孩拉上了岸。
父亲太劳累了,身体因此败得早。50多岁时得了严重的气管炎病,冬天特别受罪,扛不动粮包了,翻不动地了,拉不动和他相伴的双轮车了。农历龙年五月十八(2012年7月6日),他离开了我们。父亲的墓向南,左右有两棵绿柏树。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前去挂上粽子,献上一捧花,插上飘带,烧上一炷香,以寄托对父亲绵长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