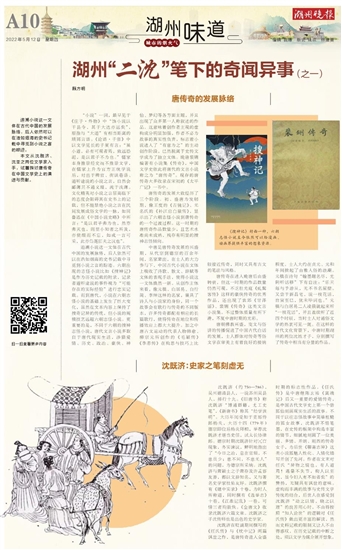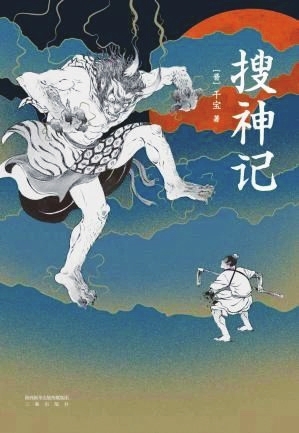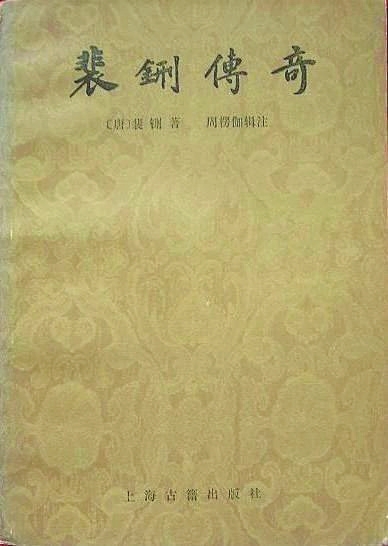顾方明
追溯小说这一文体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脉络,后人依然可以在浩如烟海的史书记载中寻觅到小说之言的踪迹。
本文从沈既济、沈亚之两位文学家入手,试着探讨唐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演进与贡献。
唐传奇的发展脉络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中“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原指与“大道”有相当距离的琐屑言语。《论语·子张》中以文学见长的子夏有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儒家本身推崇经史而不推崇文学,在儒家上升为官方正统学说后,对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之言,自然会鄙薄其不通义理,流于浅薄。文化精英对小说之言居高临下的态度会阻碍其在史书上的记载,但不能禁绝小说之言在民间发展成俗文学的一脉,如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言:“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追溯小说这一文体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脉络,后人依然可以在浩如烟海的史书记载中寻觅到小说之言的踪迹。六朝出现的志怪小说比如《搜神记》是作为历史记载的附录,记录者道听途说的事件视为“可能存在的实际经验”进行忠实记载。而到唐代,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在文本内容上保持了搜奇记异的传统,但小说的规模技艺远超六朝志怪小说。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六朝的搜神志怪小说,唐代文言小说多取自于唐代现实生活,涉猎爱情、历史、政治、豪侠、神仙、梦幻等各方面主题,并且出现了众多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这意味着创作者主观的虚构成分明显加强,作者不必为故事的真实性负责,标志着小说进入了“有意为之”的主动创作阶段,已然脱离于史传文学成为了独立文体。晚唐裴铏编著有小说集《传奇》,中国文学史依此将唐代的文言小说称之为“唐传奇”。现存的唐传奇大多收录在宋初的《太平广记》一书中。
唐传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盛唐为发轫期,像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显示出了六朝志怪小说到唐传奇的一个过渡过程。这一时期的唐传奇作品数量少,且艺术水准尚未成熟,残存有明显的搜神志怪倾向。
中唐是唐传奇发展的兴盛期,从代宗到德宗的百余年间,名家辈出,在士人的大力参与下,中国古代小说在文体上吸收了诗歌、散文、辞赋等文体的表现手法,使得小说这一文体焕然一新。从创作主体来看,像元稹、白居易、白行简、李绅这样的名家,兼具了诗人与小说家的身份,同一个故事会有歌行与传奇的不同版本,许多传奇都配有相应的长篇歌行,使得传奇在地位和传播效应上都大大提升。加之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所创作的《毛颖传》《李赤传》在构思与技巧上比较接近传奇,同时又具有古文的笔法与风格。
唐传奇在进入晚唐后由盛转衰,但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仍然可观,不乏杜光庭《虬髯客传》这样的豪侠传奇的优秀作品,还出现了袁郊《甘泽谣》、裴铏《传奇》这类文言小说集。不过整体质量有所下滑,不复中唐时期的光彩。
唐朝佛教兴盛,变文与俗讲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古代白话的发展,士人群体对传奇等俗文学在审美上有着良好的接纳程度。士人大约在贞元、元和年间掀起了由雅入俗的浪潮。元稹在诗句“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下有自注:“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稹与白居易二人凌晨就起来听“一枝花话”,并且连续听了近四个时辰,当时士人对通俗文学的热衷可见一斑。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中唐时期湖州的两位沈姓才子,分别撰写了传奇中相当有分量的作品。
沈既济:史家之笔刻虚无
沈既济(约750—786),吴兴德清县人,一说苏州吴县人,排行十九。《旧唐书》称沈既济“博通群籍,尤工史笔”,《新唐书》称其“经学该明”。大历年间受知于吏部侍郎杨炎,大历十四(779年)德宗即位后杨炎拜相,举荐沈既济才堪当史任,试太长协律郎。德宗时期沈既济针对冗官现象,务实谏议,鲜明地指出了“今日之治,患在官烦,不患员少;患不问,不患无人”的问题,为德宗所采纳。沈既济与萧颖士之子萧存及许孟容友善,都以文辞知名,又与著名史学家杜佑友好。沈既济撰有《建中实录》十卷,为时人所称道,同时撰有《选举志》十卷,《江淮记乱》一卷,可惜三者均散佚。《全唐文》收录沈既济六篇文章。沈既济之子沈传师也是出色的史学家。
沈既济在贬谪期间撰写的《任氏传》与《枕中记》两篇讽世之作,是唐传奇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性作品。《任氏传》是中唐继陈玄祐《离魂记》后又一重要的爱情传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借狐仙刻画现实生活的故事。不同于以往志怪故事中简单粗糙的狐女故事,沈既济不惜笔墨,在史传的框架中构造丰富的情节,细腻地刻画了一位美丽、多情、开朗、刚烈的传奇女子,为后世《聊斋志异》这类小说狐魅人性化、人情化描写开创了先河。作者在文末对任氏“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的赞扬,无疑具有讽世的意味。虚构而丰满的故事与史传文学传统的结合,后世人在感受到沈既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良苦用心时,不由得按照“知人论世”的逻辑对《任氏传》做出更丰富的解读,然而史料记载的限制又让人不由得感叹,在历史记载的中断之处,须以文学为媒介展开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