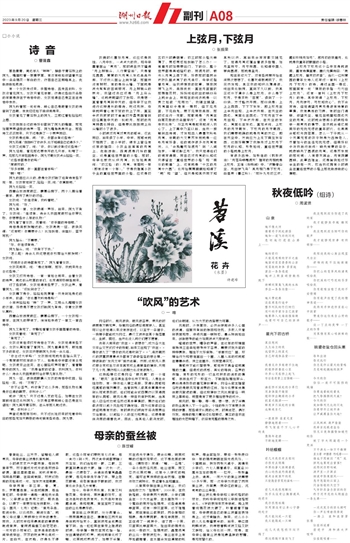○ 张振荣
孩提时代喜好月亮,这应该是共性。八月中秋,一点点大的我,和母亲靠着窗台“赏月”。那时候自然不懂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只是看见圆圆、黄黄的大月亮从东边冉冉升起,不过我从窗台上向东望,那里并没有柳树,有的是马头墙,下面就是波光粼粼的百间楼河。月上柳梢头的辰光,我望过去应该是“月上马头墙”。这就使期望打了折扣。我是想一直看着月亮到中天的,但母亲不让我进行这种漫长的等待。吃过月饼,母亲就哄着心有不甘的我上了床,直至半夜我尿尿时才偷偷打开蠡壳窗看到已经高挂中天的一轮皎月。那时的月亮特圆也特白,但是要比刚刚爬上马头墙时小了很多。
小时候对月亮对赏月的感受,仅此而已。后来读了小学、中学,那感受就不相同了。在小学时,课本上曾经有这样的插图:小孩坐在弯弯的月亮上,优哉游哉,四周满是闪烁的星空。这是童话世界里的小船。那时,母亲也教我认识月亮,比如她常常说:“初三格(的)月亮,有搭呒一样(即有没有一个样)。”于是我推算小孩子坐的童话世界里的小船,应该是初五初六时最惬意;初三时那小船太单薄了,晃悠晃悠地折断了怎么办?一弯眉月时如果要出门、下硚口,整个世界都是黑咕隆咚的。而满月时,银光从月亮上洒下来,好像那时居民会夜防队里点亮了的汽油灯。母亲还指着月亮,给我讲嫦娥的故事,嫦娥阿姨飞上天,吴刚叔叔一直在月宫里砍那棵桂花树,妈妈说他砍出的缺口马上就会合上,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以贯之地做“无用功”。我隔空眺望,月亮里似乎是有一棵树,但不见月宫,不见白兔,更不见嫦娥吴刚。那时还流行一支歌,那歌词是“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还有“月亮走我也走”,反正月亮是越来越深入我心了。上了高中乃至以后,当我一接触到古诗词,才发现古人最喜欢吟咏月亮。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就是一位咏月爱好者,他的词作很多与月亮有关。从“会挽雕弓如满月”到“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只觉得他们的词写得美,而自己对月亮的认知还只停留在“童话世界的小船”和“美女的蛾眉”上,还有就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也开始模模糊糊地知道了“朔”和“望”,但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再后来会写写散文随笔了,觉得月亮还蕴含着很多哲理,如月盈则亏,月亏则圆。也知道中国人崇尚圆满,那就是盈月。
现在年纪大了,对有些问题开始往深层次想想了,也喜欢追根溯底了。我突然发现,其实我的知识浅薄得很。说出来也惭愧,直到不久以前,我其实还分不清什么是上弦月,什么是下弦月。于是求助“百度”,读到了一个口诀,方才豁然开朗。那口诀是:上上上西西,下下下东东。即上弦月在上半月出现,上半夜升起,在天空的西边,亮面也在西边;下弦月在下半月出现,下半夜升起,在天空的东边,亮面也在东边。直观点说,上弦月的月牙朝东,下弦月的月牙朝西。我们需要明确的就是月亮的方位,即在天空中,方向应为上北下南左东右西。这刚好颠覆了我原先对上弦月下弦月的认知。形象地说,童话世界里的小船就是上弦月。
有很多古诗,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描写的月相就是上弦月。王维《鸟鸣涧》中,“夜静春山空。月出惊飞鸟”其月相乃是下弦月。白居易《暮江吟》:“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如弓”,即月初的娥眉月,也就是我童年时眼里的小船。
上弦月下弦月这个名字本身就很美,富有诗情画意。唐代元稹诗曰:“微露上弦月,暗焚初夜香”。当代一位叫黄茜的青年女诗人还写过一首叫《上弦月 下弦月》的诗,得过全国一等奖,那里面有一句“嫦娥的手指一勾勾出上弦月”。还有一首叫《上弦月下弦月》的诗,其中写道“上弦月,下弦月,月月惊弓,弓弦知我心”。我不会写诗,但觉得望月赏月是很有诗意的事情。我有晨练的习惯,有时出门得早,仰望天空,唯见启明星和西边天空的月亮,这时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赏月的情节,自然就会追忆起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也常常会感叹光阴荏苒,怎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转身为古稀老人。尽管如今的生活无忧无虑,但美好似乎与我渐行渐远?缺失爱妻的日子,就像缺失了圆满的月亮。还是苏东坡的那句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还是愉快地过好余生的每一天,权当我还拥有小时候坐在童话世界的小船上那优哉游哉的心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