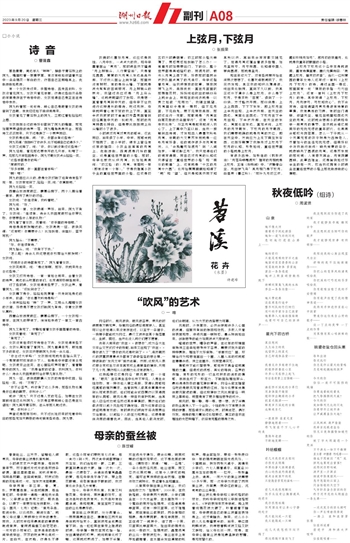○ 陈世峰
春蚕吐丝,丝方尽,留赠他人御寒风。母亲的蚕丝被是秋蚕所制。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蚕。每到养蚕季节,村子里成片成片的桑树枝条舒展,盖住屋前屋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在田间巷陌,村民们扬起的笑脸连成一片,如东方绚丽朝霞。
母亲养蚕一年三季,春,夏,秋。罗敷喜桑蚕,采桑城南隅,每当蚕忙时,母亲早一遍晚一遍地去采桑叶,父亲便会在息养之时,剪去桑条,以便下一季更好地发枝散叶。《诗经·国风·七月》记载:“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踦彼女桑”,就是父母这辈人男耕种女织布的景象。而我,儿时放学归来最常做的事便是跑进蚕房,看爬满扁框又白茫茫的、一片片的小可爱们,在绿油油的桑叶间穿进穿出,莎莎的吃食声也连成一片,在白天,在夜晚,仿佛永不停歇。这些小可爱们要吃足七次食,每一食约3到4天,两次食中间都要睡2天左右,我们当地称一眠、二眠、三眠直到最后的大眠,睡一次长一次。最后一次便老了,会通体透着亮晶晶的黄,每见母亲洗干净了手,带上老花眼镜,将老蚕端详于眼前时,我对蚕也会多生几分爱意。
如今,母亲只养秋蚕。秋蚕又叫桂花蚕。母亲说,茧质量的好坏,往往与桑叶的优良有关,秋天桑叶有白露泽润,柔和肥厚,蚕宝宝吃了后吐出的丝也是最好的。
蚕在吐丝作茧时,纷纷傲着头,一层层围裹住自己,慢慢地三两天后身体就开始变小,直到被完全包裹住看不到。当一粒粒茧在蚕笼上挂满的时候,母亲摘一颗放在耳边摇一摇,发出清脆的咚咚声,就说明蚕化成了蛹,这茧就成熟透了。如果不采摘,放在透光干燥处,便会化蝶。破茧成蝶的过程我观察过,这不是优美的神话,《博物志》写道:“蛹,一名魂”。一条小虫历经风雨,吐丝结茧,而又忽然化茧成蝶,这样令人惊叹的蜕变,循环往复独特的生命历程,在静与动之间转化,象征着永生和重生。
从蚕茧中抽出蚕丝叫缫丝,我们当地称之为“扯棉兜”。2006年,在我新婚前,母亲煮两大锅茧,乡亲们围坐在一个大木盆旁,在水里拨开一个个雪白的茧开始扯棉兜,这些通常是单宫茧。还有一种双宫茧,这不难理解,即在蚕吐丝做茧时,两条蚕相依相偎,是夫妻同眠,是兄弟同根,反正住进了一间房子,结了同一个茧。双宫茧比单宫茧大,扯出来的棉兜也会比一般的大。扯棉兜时,晶莹透亮的丝线一根根被拉长,蚕丝在手上有序地翻腾着,在水里会发出清脆的呱呱声。等全部扯好,要将一张张像口袋一样的棉兜晾晒在阳光透风处,一个星期后,拼好两张大桌子,再请来乡亲们,六七人围着桌子,将直径30厘米左右的棉兜一一拉开,一张张叠上去。通常,一床六斤的蚕丝被需要50多斤茧,那一次母亲为我做了两床蚕丝被,外面裹一层染红的蚕丝,沉甸甸的丝丝牵挂。
蚕丝被也是母亲和父亲成婚时的嫁妆。我听母亲说她和父亲刚结婚那会儿,4岁的表妹来家走亲戚,晚上哭着说棉花被太硬了,吵着闹着不睡觉,母亲便把自己的蚕丝被盖在表妹身上,这才肯睡去。原来,这么小小的人儿也是懂享受的。后来,单位团购鸭绒被,我寻思着鸭绒被又轻又软又暖和,给父母也买一床,可是,在母亲心里蚕丝被是她最温暖的慰藉,是无可替代的。